欧洲“15分钟城市”的实践与反思

2024年10月9日,在法国巴黎,一名女子在塞纳河畔跑步
文/《环球》杂志记者胡艳芬
编辑/林睎瑶
巴黎第十一区一条原本并不起眼的人行道被拓宽了,还新增了绿化带和座椅,局部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傍晚时分,附近社区的居民三三两两推着购物车穿过街角,孩子们骑着自行车在低速车道里穿梭。改造之后,街巷的生活温度似乎有了显著上升。
这是“15分钟城市”理念在现实中的一个切片。在欧洲,“15分钟城市”概念在巴黎市长安妮·伊达尔戈的大力推广下声名鹊起,她将其作为城市绿化和减排的核心策略。其愿景是:让城市居民在步行或骑行15分钟的范围内,就能满足工作、购物、医疗、教育和休闲等日常基本需求。这似乎是终结汽车中心主义、恢复社区活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完美方案。
然而,在过去5年里,巴黎在“15分钟城市”理念下的诸多试点与政策调整,一方面成为了一些欧洲城市争相借鉴的标杆,但另一方面也成为争议焦点。
“15分钟城市”理想
“15分钟城市”概念的现代推手是法籍哥伦比亚裔学者卡洛斯·莫雷诺,他将这一愿景命名为“计时城市主义”。他提出,“我们应根据人类的时间维度来规划城市,让‘好生活’的体验触手可及。”
莫雷诺提出这一强调“邻近性”和“多功能混合”的城市模式,脱胎于一系列历史上的规划思想:早在19世纪末,英国城市学家埃比尼泽·霍华德就提出了“花园城市”理念,强调将城市和乡村的优势进行结合,实现社区的自给自足;美国社会学家克拉伦斯·佩里在1929年提出“邻里单元”理念,即根据学校确定邻里的规模,过境交通大道布置在社区四周以形成边界,在邻里中央位置布置公共设施,在交通枢纽地带集中布置商业服务;20世纪末兴起的“新城市主义”运动,则强调可步行性、多样性和传统城市结构。
莫雷诺将上述这些理念与当下的气候变化和社会隔离问题相结合,提出了一个更具可操作性的框架:居民应在15分钟的步行或自行车骑行时间内,获得六大核心功能:居住、工作、商业、学习、医疗/健康和休闲。
“15分钟城市”理念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是20世纪汽车中心主义规划模式给城市带来的三大痼疾:环境危机与交通拥堵、社会隔离与生活质量下降,以及城市扩张与土地利用率低。
现代城市规划将住宅、工作和商业场所分隔,导致人们不得不依赖私家车进行长距离通勤。这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碳排放和交通拥堵。“15分钟城市”通过分散城市功能、鼓励步行和骑行,以实现城市深度脱碳。
长途通勤占据了人们大量时间,挤压了社交、休闲和家庭生活空间。大规模的睡城(依附于大城市、以居住功能为主导的卫星城)缺乏工作机会和商业设施,导致社区活力不足和社会凝聚力下降。而“15分钟城市”试图通过构建“完整社区”,将“浪费在路上的时间”重新还给居民,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汽车时代延伸着城市的半径,推动城市不断扩张,同时也消耗了大量土地,推高了基础设施建设成本。“15分钟城市”则通过提高社区密度和城市功能的混合程度,实现集约化发展,提升土地利用效率。
从某种意义上说,“15分钟城市”是一种以人为尺度的再城市化理念。它不是要把城市用围栏切割成若干封闭的区间,而是要以“时间可达”为中心,重构城市功能分布、交通系统和公共空间布局。
从“巴黎共同体”到街区试验
多年前,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巴黎塞纳河畔有一条普通的城市公路,日均车流量超过4万辆。这条路同时存在着高峰时交通拥堵和车速过快的情况,安全隐患显著,通行不便。此外,在2014年到2016年间,巴黎市的空气污染指数一直居高不下,超过欧盟标准。
于是,在2016年,巴黎市政府将这条路改造成一个“禁止车辆通行”的沿岸公园。如此一来,工作日里,上班族可以放心通行;周末时,居民和游客可以来此休闲。这是巴黎打造“15分钟城市”的其中一例。如今巴黎已是“15分钟城市”在欧洲最具代表性的实践场域之一。
最初,巴黎市长伊达尔戈在其“巴黎共同体”治理平台中明确提出了“15分钟城市”愿景,并在2020年将其纳入其连任竞选纲领。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加快了巴黎打造“15分钟城市”的步伐,疫情期间,巴黎市政府迅速将部分道路临时改为自行车道、扩大人行步道的范围、开辟户外公共空间。
此后,巴黎进一步推动基础设施投资,推进自行车道网、公共交通网络优化、街区改造计划等。还将部分学校操场在非教学时间开放为社区公共空间,增强社区近邻设施使用的便利性。在住宅密集但功能偏弱的街区推动混合开发,让商铺、社区服务和文化设施更均衡地分布。
巴黎的“15分钟城市”改造不只是基础设施等硬件上的重塑。为了切实掌握改造的效果,巴黎市政府与学界合作,将“15分钟可达率”作为绩效指标,细化到各区、各街区层面。通过地理信息系统分析、出行调查、空气质量监测等方式评估政策效果。
据英国《卫报》报道,为防止商业租金上涨将当地中小商户挤出,巴黎还设立了市属商业运营公司,对核心街区中的零售商铺租金进行调控或补贴。幼儿托育、医疗、文化中心等社区服务设施的投资也被纳入预算优先项,以促进“近邻服务”落地。
随着巴黎的实践逐步深入,欧洲其他国家,以及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也参与其中。尤其是巴黎让公众参与“共建”的做法,更凸显出前瞻性和公开性。据《华盛顿邮报》报道,2025年3月,巴黎举行了一次针对16岁及以上居民的非约束性全民投票,投票结果显示近66%的人支持一项提案:为巴黎20个区的每个街区增设5至8条新的绿化步行街。这一举措被视为推进“15分钟城市”理念的新一轮公众参与尝试。
不过,巴黎也在推进交通改造的过程中遭遇到“路网困境”、出行拥堵、配送物流调度困难等挑战。2025年9月,《黎明报》报道,巴黎在限制车流与街区改造中引发部分道路拥堵、配送压力增大等抱怨。
欧洲的实践
在巴黎之外,欧洲多座城市也在以各自的方式探索“15分钟城市”的发展之道。
西班牙巴塞罗那是欧洲最早实践“15分钟城市”理念的城市之一,其“超级街区”计划堪称典范。该计划将相邻的9个街区整合为一个大型单元,限制汽车通行,释放公共空间,用于建设绿地、儿童游乐区与步行道。巴塞罗那的目标是将城市机动车交通减少20%,并将更多公共空间还给居民。
意大利米兰则在新冠疫情后迅速提出“开放街道计划”,将35公里道路改造为自行车道与步行区,鼓励居民以非机动车方式通勤。米兰的“15分钟城市”试验体现了疫情时期的城市反思——如何让居民在更小的生活半径中完成工作与社交,从而减少通勤压力与碳排放。米兰的创新在于将“15分钟城市”与可持续交通政策相融合,通过公共交通、共享单车与城市绿化系统的协同,塑造一种更具“流动性”的15分钟生活方式。

人们在意大利米兰附近的水边戏水消暑
丹麦首都哥本哈根长期以“全球最宜骑行城市”著称,政府提出“绿色半径”概念,以骑行网络为核心,将教育、健康、娱乐与商业设施均衡布局在居民区周围。
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15分钟城市”建设更具有技术特色。政府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AI)算法,对居民出行模式、公共服务分布和公共资源利用率进行分析,从而动态优化城市布局。赫尔辛基提出“智能邻里”模型,如卡拉萨塔玛新区,通过数字平台让居民实时查询社区服务、共享交通与能源使用情况。总体来说,赫尔辛基强调技术赋能与居民参与的共治机制,使“15分钟城市”成为数字社会治理的试验场。
反对声中的反思
需要指出的是,在巴黎、巴塞罗那等地被视为进步典范的“15分钟城市”,在欧洲部分国家乃至北美的某些圈子,却受到强烈抵制,甚至面临充满敌意的“阴谋论”攻击。
比如,英国牛津郡议会曾提出一项交通过滤系统,旨在减少车辆穿越市中心的数量,提高公共交通效率。反对者却声称这是限制市民活动自由、将他们“困在”自己的社区,并需要数字通行证才能外出的阴谋。
英国还有一些低流量街区——通过设置障碍物(如花盆或自动伸缩柱)阻止车辆在次要道路上通行,以创造更安静、安全的步行和骑行环境。抗议者认为这损害了驾车者的权利,人为制造了交通不便,伤害了社区内的商家。
在这些抗议声中,“15分钟城市”甚至被描绘成一个“开放式监狱”,是“全球精英”推行的“气候封锁”和“社会控制”工具。
这种激烈的反对声音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源自社会对经济现状和未来的焦虑、对政府的不信任以及政治极化。在欧美汽车文化根深蒂固、强调个人行动自由的社会中,“15分钟城市”被视为一种对自由主义的背叛。尤其在英国和美国,驾车出行被视为一种基本权利和个人成功的象征。任何限制汽车使用的政策,即使目的是改善环境和公共健康,也会被视为侵犯个人自由。还有一些人认为,政府正在利用气候议程来限制他们的生活方式和选择。
反对声中也夹杂着一些合理的担忧。比如,有些人认为如果社区改造和设施升级仅发生在富裕地区,或者导致当地物价和租金上涨,那么有可能导致中低收入群体被迫离开原有家园。
而对于城市郊区和农村地区的居民来说,他们可能已经习惯于依赖汽车出行,“15分钟城市”的理念似乎与其生活环境格格不入。他们担心资源将集中于城市中心,而他们生活环境的改善将被忽视或边缘化。
因此,让“15分钟城市”这一理念成功落地,实施者必须在公平性和沟通透明度上做足功夫。
莫雷诺理念的四大支柱之一,即“普遍性”,强调的就是所有居民,无论收入、种族或能力,都能平等地获得这些便利。
这种理念要求,首先,地方政府必须引入强有力的反绅士化政策(城市绅士化是一种社会空间现象,其特征是城市中产阶层以上阶层取代低收入阶层重新由郊区返回城市中心区),例如租金管制、保障性住房的严格配建,以及社区土地信托等机制,确保社区改造的红利能惠及所有现有居民。
其次,要优先投资“欠发达”地区。将投资重点从已经完善的市中心,转移到服务不足的边缘和低收入社区,通过提供新的绿地、医疗中心和优质学校来实现资源的再平衡,从根本上解决最初导致不平等的功能分区问题。
此外,还要兼顾身心障碍和老年人群。确保“15分钟生活圈”的便利性不仅是物理距离上的,也是无障碍的,包括平整的人行道、充足的休息设施和便于使用的公共交通。
而面对政治化指责和阴谋论的冲击,城市决策者必须采取更透明、更具包容性的沟通策略。比如,巴黎经验中鼓励居民“自下而上”式地参与设计。政府在设计新政策前,与社区居民,尤其是驾车通勤者、小企业主和边缘群体进行广泛、真诚的对话,共同决定“15分钟”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以本地可接受的方式来实现。
总体而言,欧洲“15分钟城市”的争议,本质上是一场关于城市未来发展方向的价值观之争:是继续坚持以私家车为核心、效率至上的郊区化蔓延模式;还是回归以人为尺度,强调健康、社区和环境可持续性的紧凑模式?
在气候变化和能源危机的双重压力下,欧洲城市不可能倒退回汽车中心主义的时代,因此“15分钟城市”的理想并未破灭。未来,欧洲的城市转型将不再仅仅是技术和规划的较量,更是一场由耐心、信任和社会共识构建的长期博弈。只有当邻近性真正成为普遍的权利,而不是阶层的特权时,这一理念才能最终克服阻力,实现其“幸福邻近性”的初衷,真正成为下一代可持续城市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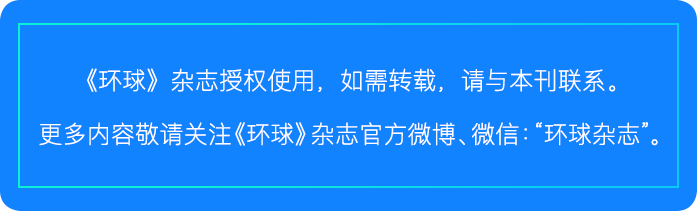

 手机版
手机版